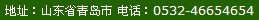|
北京最佳酒渣鼻医院 http://pf.39.net/bdfyy/bdfzj/210310/8733680.html 一 喜鹊鹊出窝窝还在, 什么人留下个走口外? ——河曲民歌 蒲棒儿她们村叫罗圈堡,小村子高高地挂在山尖子上。一圈土城墙把十几户人家围在城堡里,人就象住在桶里头一般。堡里有兵士们住过的土窑,有一墩顶天立地的烽火台。堡墙和烽火台上,不时能找到生锈的铁箭头。从堡里能看见黄河水沿着山脚慢悠悠地流,河那边就是口外了。每年三春期黄毛儿旋风一刮起来,蒲棒儿她爹就该出口外揽活去。蒲棒儿她娘早早就说,咱可说得好好地,到时候我可不送你。灰人呀,找上你这走西口的汉子,可把我们母女两个害苦了。扭过头来,又对蒲棒儿说,蒲棒儿你灰娃娃总算长大了。赶秋后你爹回来,给你打听个好人家,跟上男人过日子去吧。娘甚也不挑拣,就盼你找个不走口外的人。你爹走得心野了,他把咱娘儿两个害苦了。 娘年年这样说,爹年年这时节走。娘送爹送了十几年,眼看着身子瘦了一圈又一圈,蒲棒儿她爹强忍着眼泪,死活不让她再送了。这二年,送爹就成了蒲棒儿的事。 正是春寒料峭时节,冷风从河对岸的山缝儿里钻出来,贴着水面呼呼地往河这边吹。风把河里零星的冰凌吹得突罗罗地转。转着转着,或者没入水中悄悄地化了,或者翻一个跟斗急匆匆地再往前面赶去。天气凉飕飕地,但毕竟是春天了,人踩在地上,有一种暄乎乎的感觉。 象往年一样,蒲棒儿随着她爹下山以后,一路上见到的尽是些走口外的庄稼汉,他们肩挑着行李和路上的吃米,潮水般往渡口涌去。每年到了走西口的时节,镇子里照例要唱三天戏。除过三场大戏以外,天天加一段《走西口》。那戏文大人娃娃都会唱。日子久了,这地方连狗叫声都带点《走西口》的味儿。大约昨儿晚上戏散得迟,蒲棒儿看见男人们不住地打着哈欠,谁也懒得说话。女人们哭够了,说累了,少精没神地跟在汉子后头。一会儿,她们把男人送上船,便要折转身子回村去,好歹把一年的日子撑持起来。汉子既然要走,就得早些些动身,一来路上有个伴儿,二来也能租到口外的好地。至于口里那些瘦坡地,反正打不下几颗粮食,有她们和娃娃们作务就行了。 蒲棒儿和她爹来到河畔时,装满各种货物的大船已经准备上路了。众船汉穿着单衣单裤,听见艄公一声吼喊,便齐刷刷地背起襻带,把结了疙瘩的小绳头儿一甩一拽,准准地缠在绷直的纤绳上。随后双手撑着地面,杭唷杭唷地呐喊着,一步一步地朝龙口方向爬去。另外十几支运人的船只,也一齐解开缆绳,吆喝人们赶快上船。艄公挺立船头,眼瞅着人上得差不多了,便从嘴里拔出旱烟锅子,在舵杆上吧吧一磕,人们立时安静下来。有人把缆绳使劲扔到船上,船滴溜溜地在水面上转了半个圈儿。这时侯,艄公把旱烟袋插进腰里,扬起脖子猛然唱一声:众妹子——船汉们嗨地一声抓紧腰棹,脚往船板上一蹬,身子朝后面一仰,大船嗖地一下离了岸,转眼间就到了河中心。艄公不紧不慢地摇着舵把,接着唱道:——快快儿回!风大吹了你那白脸脸,沙土迷了你那毛眼眼。守住身子护住门,等哥回来过大年! 船汉们嗷嗷地和着,把两支腰棹舞弄得如飞龙一般。河水哗哗地溅到船上,人们左躲右闪,再也顾不上张望河畔那群送行的女人们了。 不到一袋烟工夫,船靠在河对面准格尔旗岸边。那时候蒲棒儿心里就想,那就是个口外?和河这边一样样儿地,可有个甚的走头呢? 她好像听见爹在河那面喊:“回吧,女子。爹——秋后就——回来了——” 她看见人群往对岸的山上爬去。不一会儿人变成黑点点,象蚂蚁一样翻过山那面去了。她把眼睛眯成缝儿,能看见一条小路,能看见人们走出去的一道沟。她又听见那凄凉的山曲儿了:哥哥你走西口,小妹妹实在难留。手拉着哥哥的手,送在哥哥大门口。坐船你要坐船仓,你不要坐船头…… 每到这时候,蒲棒儿就想起娘的话。娘让她找一个不走口外的男人,可她长这么大,还没见过这种庄户人。人的命,老天定。生在这种十年九不收的灰地方,男人就得走口外,女人就得在家里守着盼着熬着。要想亲亲热热厮守着,一家老小就得把锅吊起来。蒲棒儿想,要是日后找个汉子,正月里成了亲,二月就得送他走口外。与其在家里瞎想,还不如跟上那人一起走。不信口外那狼虫虎豹就专吃口里的女人。不信女人就种不了蒙古人那地。实在走不动了,就雇一头驴。说是穿过鄂尔多斯毛乌素大沙漠,口外后大套的土地肥得流油哩,雇一头驴能花几个钱?爹说,罗圈堡离包头城,总共就七天的路程。问怎么个走法,她爹就给她唱:头一天住古城,走了七十里整。路程不算远,跨了三个省。第二天到纳林,碰见几个蒙古人。说了两句蒙古话,甚也没听懂…… 二. 麻阴阴天气雾沉沉, 想亲亲哭成个泪人人。 ——河曲民歌 深秋时节,走西口的人们就要回来了。 河畔人山人海,挤得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。蒲棒儿和她娘一靠近人群,就被圈到人堆里。灰皮男人们眼尖,一看见来了个水灵灵的大闺女,立马象浆糊一样粘过来。母女两个被挤得出了一身汗,脚被踩了,身上爬满了手。娘大声笑着骂着,两手使劲挡着人群,时不时抬腿踢一脚,有人就哎哟哎哟地呻吟着,弯倒腰退走了。 一会儿,羊皮筏子顺河漂下来。先是一只两只,随后就漂满河面。筏子是从口里背到口外的。小雪时杀了羊,把羊皮整剥下来,展展地贴在墙上。过罢年,用桐油泡透,放在阴凉处让它风干。三春期旋风一起,男人该走口外了,女人便把缝好的羊皮叠进铺盖卷儿里。过沙漠时是水袋,睡觉时是褥子。等到回来,便成了装粮食的口袋。把口袋拴在一起,便是一排排筏子。把筏子放到大河里,任它漂,任它流,一滴水都渗不进去。 筏子一靠岸,人们解开筏绳,把羊皮口袋提上岸,有人用刀子割开羊皮,里面装满红丢丢的糜子。有长者把糜子撒进河里,岸上的人便高声喊道:“河神爷爷吃来哇!河神爷爷吃来哇!” 除过撑筏子的,其余的人都坐船过河。大船一支支靠岸,蒲棒儿眼瞅着一家子一家子喜喜乐乐离开河畔回家去了,就是没她爹的人影子,便对娘说:“说不定是明后天那一拨。”娘笑着说:“你爹那灰人,一准是让蒙古女人绊住啦。其实有合心思的,引回来就是了,也让咱娘俩开开眼,看看稀罕。” 到了后半晌,河畔的人越来越少,娘有点沉不住气了。她捯着两只小脚,一会儿跑到河边问船家,一会儿拦住那些忙着回家的人。人们都说,没碰见,一路上就没碰见你们罗圈堡的人。娘叹了一口气,盘腿坐在河堎上。 已经是霜降时节,深秋的风从河那面吹过来,嗖嗖地直往人脖子里头灌。太阳很快出溜到山背后,河面上罩了一层厚厚的雾。船汉们挽紧缆绳,说是要到城里头找个女人红火红火去。一群没接着汉子的老婆们,相互间搜肠刮肚地说着宽心的话。天渐渐黑了。路远的忙着进城找歇息的地方,路近的也陆续回家了。河畔只剩下蒲棒儿和她娘。娘好像变成一个瓷人儿。她紧抿着嘴唇,身子一动不动,只一双眼睛死死地盯住河那面。 天完全黑了。山影子倒在河里,河面一片漆黑。河水哗哗啦啦地往前流,响一声,人就禁不住抽搐一下。 蒲棒儿紧紧挽住娘的手,说:“娘,咱回吧。我爹年年走,年年平平安安回来。那条路他闭着眼睛也能摸得见。咱回吧,咱明儿再来。” 娘哑着嗓子说:“回吧……” 一路上,娘儿俩谁也不说话。路过娘娘庙,娘拉着蒲棒儿的手,摸黑进去磕了头。出了庙门,娘说:“蒲棒儿,娘把你生错了。你记住,这辈子但有三分奈何,千万不要找走口外的人。下辈子你要是有福气,就转成个男人!” 蒲棒儿扑哧一笑,说:“那还能由了我?我还想上天哩,谁给我搭那梯子?” 转眼就立冬了。 西北风呼呼地刮起来,河面上立时漫下来一层细碎的凌片。蒲棒儿母女天天到河畔接人,眼看着河那面小路上人走尽了,扳船汉们把木船一支一支抽到岸上来。人们起先还逗这母女两个,说可惜了那么好的一片水地闲闲地放着,倒不如先请个顺眼的男人种着,等你家主子回来了,我们悄悄地躲开还不行?蒲棒儿朝他们呸呸地吐唾沫,娘好象甚么也没听见,眼皮不眨地盯着满河的冰凌。 船汉们后来甚么也不说了。他们紧盯住这娘儿俩,随时准备下河救人。 蒲棒儿她娘心里着急,吃不下,睡不着,嘴边烧起来一串串燎泡。人到这种时候,或许就真的迷了心窍。越是接不着,就越是要去接。每天天一亮,她就挣扎着下了地,拄起棍子就走。 娘儿俩天天往河畔跑,天天眼巴巴地盯着满河的冰凌。娘把一盏盏灯碗儿放在冰凌上,俩人跪在河边,一遍遍祈求河神保佑,保佑蒲棒儿她爹平平安安地回来。娘嗓子哑得没声了,还是张着嘴一个劲儿地喊:“灰人,你回来吧!你可不敢把我们母女两个闪下了!回来吧,亲人,回来咱热热乐乐过年,咱再也不跑口外了!” 蒲棒儿哭着应道:“回来了,我爹回来了,我爹再也不跑口外了!” 那时候冰凌咯吱咯吱地磨着牙,就理也不理她们娘儿俩。一阵阵穿河风刮过来,冰凌冷着脸把灯碗儿都驮走了。 蒲棒儿哭着对娘说:“娘,你回去吧,我等我爹。” 娘摇摇头,有气无力地说:“就是死了,我也得看见他的骨殖呀!” 蒲棒儿说:“说不定我爹遇上土匪了。咱想开些些,大不了把一年的工钱抢去,土匪是要钱哩,他又不要命。” 话是这么说,蒲棒儿心里直发沉,隐隐约约觉得事情有点不对了。 三. 你走那天天有点阴, 响雷打闪不放心。 ——鄂尔多斯漫翰调 蒲棒儿她爹还真是遇上土匪了。 在后套结算工钱时遇到些麻烦,他比往年迟动身半个多月。到了包头城,他用工钱买了几两洋烟。随后回到二里半的留人小店,背着人一小点一小点黏在皮袄的毛缝里。黏完之后,又到茅坑里挑了些粪便,闭住气胡乱涂在皮袄里面。 第二天一早,他跑到包头街上,四处打听往口里起灵的人。 早以前朝廷就立下规矩,不准口里汉人在蒙古地界建坟。走外口的人死了,一概由各处讨吃窑里的头儿们处置。他们记下死者的名姓,用讨吃窑打造的柳木棺材装殓了,或是厝在沙子里,或是一溜一溜排在野地。刚装进去时,由讨吃窑的摸鬼行者看着,以免让狼吃了,让狗啃了。不消几个月,棺材里剩下一具干尸,摸鬼行者就撤走了。讨吃窑的头儿就坐在家里,等着主家来缴钱领尸。 蒲棒儿她爹打听到一个叫杨满山的后生。那后生是河曲县火山村人氏,说来是杨老令公杨业的后人。后生长得高高大大,两道浓眉间,隐隐还藏着几分杨家人的气势。杨满山他爹杨二能死在口外多年,终于等到儿子长大,如今要把他爹的灵柩运回去,正好和蒲棒儿她爹同路。蒲棒儿她爹对杨满山说:“叔和你相跟上回吧,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”杨满山一口就答应了。于是俩人先到讨吃窑缴了钱,又到包头街上买了红公鸡、引魂幡、引路钱等一应路上用品,然后回到二里半雇了东川人的一辆牛牛车。 夜里,蒲棒儿她爹对杨满山说:“过了乌拉素和珊瑚湾,路可就越走越凶险。虽说有灵车护着,也得防住些些土匪。满山你身上不敢带现钱,有了就换成洋烟,总比银钱好藏些。等回去再兑成钱就是了。”杨满山极是感激,一口一个叔,倒把蒲棒儿她爹叫得不好意思。 二日鸡叫头遍,棺材头上拴牢红公鸡,一行三人动身上路。东川人赶着牛牛车,背抄了手走在中间。杨满山在前头打了引魂幡,一声连着一声地哭叫:“爹,上路吧!儿我接你来了,咱父子们相跟上回家哇!”蒲棒儿她爹跟在车后面,一边撒着引路纸钱,一边接应道:“回来了,刮野鬼那灰人回来了。” 车过沙蒿塔子时,冷风把一人高的沙蒿林刮得一会儿唰啦啦地冲向南边,一会儿又唰啦啦地朝东扑过去。蒲棒儿她爹和杨满山头皮发紧,赶快掏出防身的小攮子,眼盯住四面,侧着身子往前走。 这时侯老牛仰起脖子,哞哞地叫着。红公鸡不住地抖动翅膀,大中午竟咕咕鸣咕咕鸣地叫唤开了。 六个土匪是半后晌时分从霸梁那边围过来的。 那简直就是一群讨吃鬼。立冬已经好几天了,六个人都还穿着单衣单裤。衣裤上摞着一层层补丁,缝住的贴在身上,没缝住的随了风头儿忽啦啦地飘。土匪们堵住四面的路,手里舞弄着拴了红布条的鬼头刀,叽哩哇啦朝他们喊着蒙古话。 赶车的东川人显然认得他们。他对一个土匪说:“日你祖宗个胖挠子,不想今儿就遇上了你。快不要装神弄鬼了,明明和我们一球样,你装甚的蒙古人呢?死人活人都在这里,想要甚,说话吧。” 那个叫胖挠子的土匪讪讪一笑,到棺材头前取了供养死者的倒头馍馍,噗噗噗吹掉上面的香灰和尘土,边吃边用本地汉话说:“狗的,昨儿黑夜手臭,把钱和衣裳输了个净片儿响光。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,有钱分着花吧。你们是要命呀,要钱呀?” 蒲棒儿她爹不知从哪里拿出烟锅头大的一块洋烟来,笑着说:“这回出来接老人,一路上花费不少。剩了点这东西,我也不会抽,弟兄们拿去过过瘾。” 一个土匪举着刀说:“鞋大鞋小不要走了样儿。咱依着规矩来,脱吧!” 赶车的不用脱。他的工钱存在包头,沿路费用都由雇主包了。除了一身衣裳和旱烟袋,东川人浑身不带一个子儿。蒲棒儿她爹看一眼杨满山,噌噌噌就脱光了。杨满山稍一迟疑,屁股上立时挨了两脚板子。 土匪们仔细翻检他们脱下来的烂衣裳。查完里头的裤衩子汗溻子,一使劲扔得远远地。胖挠子提起蒲棒儿她爹的烂皮袄,连忙捂住鼻子说:“妈的怎么这么臭?” 蒲棒儿她爹说:“一年四季铺的盖的都是它。前一阵子拉稀,一不小心就给糊弄在上面了。” 胖挠子一听,赶紧把烂皮袄扔到沙蒿林子里。 另一个土匪提起杨满山的皮袄,抖抖尘土,满不在乎地披在自己身上。 等俩人去捡衣服时,土匪们正在商量要不要撬开棺材。蒲棒儿她爹说:“这可使不得!要是别姓人家的灵,弟兄们瞅瞅也无妨。可这是杨家后人的灵,我看弟兄们还是不惊动为好。” 土匪们不信,杨满山少不得把火山村和几代先人的名姓数算了一番。胖挠子说:“狗日的算我们倒霉,偏偏就碰上杨家的人。欢欢儿把皮袄穿上,老令公家的东西咱寸草不沾。只是这位掌柜的能说会道,你也不姓杨,你就受上点罪,算是付了我们的跑路钱。朋友,咱们两清了!”说着,把蒲棒儿她爹按在车辕上,冲屁股就是一刀。 胖挠子把刀子捅进去,轻轻地转了一个圈儿。顺着刀路,蒲棒儿她爹屁股上的肉,立时就翻了起来。胖挠子临走时眯缝着眼睛说:“朋友,哥给你在屁股蛋蛋上栽了一朵白莲花” 杨满山牙齿咬得咯嘣咯嘣地响,提着拳头要追过去。东川人抽一袋旱烟,淡淡地说:“走吧,这不算个事情。” 杨满山蹬着眼晴说:“这怎么走?总得找个人给我叔看看。” 东川人说:“找人?这周围一百里地界,除过你们回口里的人,剩下的净是些些土匪。灰货们没要你们的命,算是给够你们杨家面子了。谁让你们回迟来?要是前些日子混着大群走,他们也没有这份胆子。” 蒲棒儿她爹说:“”满山,你给叔记住这个胖挠子。三年等狗的个闰月年,总有一天,咱得把他扔到黄河里喂鱼。走吧,这点点外伤,也要不了我的命,撒上一把香灰面面就没事了。咱走吧。” 杨满山没动身子。他看着窄小的车厢板,嗵一声跪在地上,给蒲棒儿她爹磕了一个头,说:“叔,委屈你陪陪我爹,就在他身旁挤一挤。你这是为了我爹受的制。要是土匪把棺启开,我这儿子就没法当了,我就一头撞在这棺板上了!” 蒲棒儿她爹一把捂住满山的嘴,连声说道:“那不行,那不行,不要惊动你爹。你让他一个人消消停停歇着。你放心,谁也不敢打动你爹。往远走咱不敢说,雁门关金沙滩伊克昭里外,无论汉人蒙人,谁也不会糟贱杨家的人。咱走吧,你看,我能走哩——”说罢咬住牙一迈腿,心想走出个样子来,身子却不由地一哆嗦,哎呀一声倒下了。 杨满山赶忙把他抱起来,二话不说放在棺材前面。蒲棒儿她爹挣扎着要往下跳,东川人叹了一口气,说:“我真服了你们这些口里人了!不管甚时候,都能从旮里旮旯翻腾出些烂道理来。你们也不要揪扯了,死人不会忌怪活人,你欢欢儿躺在那儿,让后生把你拴住些,省得过河槽时摔你个死蛤蟆。你们要是再拖延,我可是把灵卸下走呀。说不定一阵阵又遇上一股霍拉盖——这是蒙古话。你跟霍拉盖讲你们那臭理去,不等你讲完,他就把你那吃饭家伙旋下来了。狗的你们这些半吊子河曲人!” 一番话把两个人镇住,蒲棒儿她爹抱了大红公鸡,乖乖地躺下了。 四 山在水在石头在, 人家都在你不在。 ——河曲民歌 当杨满山把蒲棒儿她爹背回罗圈堡时,蒲棒儿她娘已经昏迷了好几天。 蒲棒儿听见大门响,以为是扎针的先生来了。她一边赶忙答应着,一边手忙脚乱地收拾炕上凌乱的东西。门外的人大声喊:“灰女子快开门,爹回来了!”蒲棒儿心里一热,噔噔噔跑出去开了门。一拉大门扇,一眼看见她爹扒在一个男人的脊背上,不由喊一声我那老天爷爷呀,两腿一软,人就靠着门扇倒下了。 杨满山赶忙先把老的背进窑洞,又赶紧跑回大门道去看小的。只见那闺女嘴里嘶嘶地出着点悠悠气,两条胳膊软软地耷拉在门槛上。杨满山赶忙过去掐住人中,那闺女醒过来,撕心裂肺地喊一声爹呀,人又昏了过去。杨满山双眼一闭,抱起闺女就往窑洞里跑。 蒲棒儿她爹顾不得伤痛,从针线笸箩里捏起一根针,先把女儿扎醒。再看炕上躺着的女人,由不得大声喊道“蒲棒儿她娘,我这不是回来了嘛,你怎就给我成了个这样儿!” 蒲棒儿她娘嘴里说着胡话,手脚直往一搭儿里抽。 杨满山说:“叔你在家守着,我进城里去请先生。” 蒲棒儿她爹说:“只怕是晚了!” 杨满山说:“先生一来就知道了。” 杨满山一走,蒲棒儿她爹赶忙提起烂皮袄,从毛缝里刮出针尖大一点儿洋烟,给女人喂上。蒲棒儿两眼发直,也不知道过来帮她爹一把。 蒲棒儿她爹看一眼破窑烂炕,看一眼老婆闺女,不由狠狠地抽了自己两巴掌,随后把头一抱,呜呜地哭了。 傍晚先生进了门,把完脉再翻翻病人的眼皮,说:“火攻心,寒火不容,神仙也没法法了!” 半夜时分蒲棒儿她娘睁开眼,一只手摸索着攥住女儿,嘴里头呜呜呜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 蒲棒儿她爹赶忙俯下身子,把耳朵贴在女人的脸上。女人似乎知道汉子回来了,吃力地抬起一只胳膊,蒲棒儿她爹一把攥住女人的手,轻声说道:“妹子,我回来了,我再也不到口外去了!” 女人挣扎着给了他一个苦苦的笑。待换过气来,说:“灰人,总算是……” 蒲棒儿扑到娘身上,娘大张着嘴想说话。嘴里却喊不出声来,她使劲一蹬腿,最后一点劲用完了,胳膊便突然一软…… 蒲棒儿她娘死的时侯,想给父女俩一个笑,可两边眼角上,却挂着两滴泪珠子。泪珠子流到她的耳畔,蒲棒儿她爹哆嗦着双手想把泪接住,可是那泪已经断了。 五 妹妹十七哥十八, 苦命人拴在一搭搭。 ——河曲民歌 蒲棒儿她娘一闭眼,蒲棒儿她爹硬撑了一天。他割开鞋底,拿出一张复盛公字号的银票,又把皮袄毛缝里的洋烟抠出来,一并交给满山,请他进城兑成钱,先把看病先生的费用付了,剩下的请阴阳、买棺材、买寿衣、买麻纸…… 杨满山一一照办,山上山下跑得脚板子冒烟。 那天一进门,他就知道自己走不脱了。他不能把这父女俩撂下。进城请先生那天晚上,他请车把式代他把灵运回村里。千里之外,能把老人平平安安地运回来,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迟埋几天,村里人不会说长道短的。 等把东西置办齐,杨满山说:“叔,你过过眼。我年轻,怕有甚的疏露。” 蒲棒儿她爹一把攥住他的手,哽咽着说:“满山,真难为你了!” 杨满山搀着他,到院里看了一眼。蒲棒儿她爹看到寿木时,不由大吃一惊。原先说好买一副柳木棺材,满山却买回来一副松木的。那副棺木材料厚实,做工精细,至少是城里中户人家用的。 蒲棒儿她爹吃惊地问:“满山,你——” 杨满山说:“叔,婶子命苦,生前没好活,如今走了,也该有个好的着落。咱成年价跑口外为甚哩,还不是为了多挣几个钱?如今钱挣回来了,人却不在了,咱要那钱做甚哩?你那钱我没动,你给蒲棒儿留下吧。我光杆一个人,埋完我爹就走呀,我再也不回这地方来了。我给我爹也买了一副松木的,忙完这里,我再回火山去。叔你也别在意,你这里事情多,我给你搭个帮手。我爹没了十来年,人早就干了,迟埋早埋一个样。”他低倒头抠着手指,不好意思地说,“叔,你知道我把钱藏在哪里来?我爹那副柳木棺板尽窟窿,我把银票填在里头了。” 蒲棒儿她爹没说话,浑身抖作一团。杨满山觉着不对劲儿,伸手一摸,人烫得尤如火炉一样。他赶紧把他扶进窑洞,褪下裤子一看,见刀口已经烂成了一团蜂窝。 要不是杨满山,蒲棒儿一家只怕那几天就要散架了。 蒲棒儿一辈子也忘不了杨满山的恩情。从那以后多少年,她在心里千遍万遍地呼喊:“满山哥!我那亲亲的满山哥呀!” 娘的后事,是满山哥一手经办的。那几天蒲棒儿昏昏沉沉,就知道哭。满山说:“妹子,你不要哭了,你再哭,我也没主意了。”蒲棒儿抽噎着说:“我娘不在了,我爹病成个那,你说我该怎办呀?我是甚的路也没有了!我不哭,我还能做甚呢?”满山说:“人活在世上,甚的事情也得顶着。我爹走口外失去音讯时,我才十来岁,你看我不也活过来了?你坐起来,你看你姑她们累成那样,你去帮她们做饭洗碗搭个下手,一会儿亲戚朋友来了,不要让人家笑话咱们。” 蒲棒儿就挣扎着下了地。满山不好意思扶她,递给她一根棍子。蒲棒儿拄着棍子到了院里,一看见灵棚里的棺材,由不得喊一声我那娘呀,人又昏倒了。 灵棚是满山哥搭的。蒲棒儿她爹说:“装殓完就放在炕上吧,让她再在这眼窑里住上几天。蒲棒儿,你娘没给你生下个兄弟,你得撑住些些。夜里多给你娘点上几炷香,多烧上些纸钱。你满山哥住的那孔烂窑,夜里走风漏气,他也歇息不好,就不要让他起来了。” 满山说:“叔,先顾活的吧,我看蒲棒儿也快顶不住了。家里头窄憋,婶子看着心里也难过哩。不如在院里搭个棚子,也好安放祭奠的吃食,人们磕头烧纸也方便些。咱如今七心八思的,万一窑里走了火,可就不好了。” 满山一说,蒲棒儿她爹就不再言语了。 祭奠用的吃食,是满山哥铺排的。他一个后生家,竟然甚也能拿得起来。没等姑姑来,他就发了面,蒸了馍馍,炸了油糕,捞了糜米捞饭。蒲棒儿问:“满山哥,你怎就学会做饭来?”满山说:“我娘去世后,我就自己过上日子了。半碗米一碗糠,我自己做粥吃。在口外这几年,我在大伙房帮过厨,我把大师傅那些些手艺全记在肚里了。咱是没东西,要是有东西,八八大席我也能做。” 把饭食备齐,满山说:“妹子,你过来,你跪下给你娘说,不孝女蒲棒儿给你老人家送饭来了。这是老人们留下的规矩。” 给娘的饭菜,都放在小碗小碟小瓯子里。蒲棒儿说:“哥,你就多放上些些,让我娘饱饱吃上几顿。” 满山说:“倒头捞饭倒头菜,有个样子就行了。放多了,婶子会心疼的。” 把娘的灵抬到院里,满山在灵前摆了供桌。蒲棒儿强撑着出去磕头烧纸,看见供桌上摆着一条羊腿。她瞪大眼睛问:“哥,这是?” 满山哥说:“这是口外的规矩,咱也学着些些。等以后有了空,我给你叨啦叨啦蒙古人的乡俗,往后遇上事心里也有个谱。” 爹的病,是满山哥张罗着治好的。他用盐水洗过伤口,再撒上些土龙骨面面。他说:“叔,按着咱在口外得病的法子治吧,你忍住些些,我动手呀。” 他叫蒲棒儿拿过一只碗来,啪一声在炕沿上磕烂,随后用白白的碗碴在病人背上划了一个叉,不等血流出来,呼一声就把火罐子拔上了。 他又捏起蒲棒儿她娘的纳底针,放在灯头上烤烤,一针一针扎在病人的十指上。扎一针,蒲棒儿她爹咳嗽一声,这样就把病咳出去了。 忙到半夜时分,满山要过那眼烂窑洞里歇息去,临走时告诉蒲棒儿:“给你爹把被子盖严实,你在窑里浇上醋炭,逼邪避寒。” 蒲棒儿乖乖跳下地,从炉子里夹出一块红炭来,把一瓯子醋噗一声浇上去,满窑顿时飘起来一股股醋味。 醋炭那味儿可真好闻呀! 六 拽住你的胳膊拉住你的手, 说不下个情由不叫你走。 ——河曲民歌 蒲棒儿她娘入葬以后,满山说他要回火山村去了。蒲棒儿一听,半天转不过弯儿来。满山哥是她们家的人呀,他怎么能说是回火山村去呢?蒲棒儿早就想好了,等忙过这段日子,她再也不让满山哥动手做饭了,她要天天变着样儿给他们吃喝。俗话说,收不收还吃一秋呢,家里刚给娘办完事筵,有的是米面,有的是猪羊肉。她爹和满山哥在口外受了一年,回来又遇上这样的事情,蒲棒儿要好好地给他们补补身子。 娘说再不让她爹走西口了。如今娘不在了,蒲棒儿要替娘拦住他们。要是不听劝说,蒲棒儿就抱住他们的大腿,就不让他们挪步子,不信能把她拖到口外去! 她把酒也留下了,足够他们喝一冬。明年三个人下力气种地,说不定能遇上个好年景。到那时侯,她早早儿又把肉和酒备下了。城里的财主能吃甚呢?还不就是个油糕粉汤糜米捞饭肉烩菜!那饭她也会做,保准比财主人家的还要香。等她缓过劲儿来,她就给满山哥用荞麦糁子蒸碗托,用山药丝丝蒸块垒,用豆面蒿籽刷次粉,用猪肉馅儿包烧麦。满山哥爱吃糜米酸粥,她每天多吃一把苦菜,满山哥就天天能吃上精米酸粥。把酸粥盛在碗里,顶顶上刨开个小坑儿,给他夹上酸烂腌菜抹上红盐汤,给他用胡麻油泼辣椒面儿,让他端着碗到大门外去吃,一准把满村的人都馋坏了。 谁做的?当然是知冷知热的蒲棒儿! 她也不让满山哥在那眼烂窑里住了。男人家受上一天苦,全凭黑夜好好地歇缓歇缓。可那眼烂窑洞就不是个住人的地方。昨儿晚上她爹说:“蒲棒儿,你到那眼窑里苟且着睡上一夜,我和你满山哥今儿黑夜喝酒呀,你就不要过来了。”蒲棒儿摆好饭菜,就进了那眼烂窑。她在炉子里加上炭,眼看着火苗儿呼呼地往上窜,窑里就是没有半点儿热气。她咬紧牙钻进被窝里,一黑夜冻得直哆嗦。 那不是窑洞,那简直就是一座冰窖。等开了春,让她爹好好整拾整拾,她就能搬过去了。到时候让满山哥住到正窑,跟她爹边喝酒边叨啦口外那些陈年旧事去。要是满山哥不愿意,就把烂窑锁了,三个人住在一搭搭。到了晚上,学人家蒙古人的样儿,在留宿的男女之间,直直地放上一根红裤带,就甚的顾忌也没有了。 直到杨满山出了大门,蒲棒儿才知道她盘算的净是些瞎道道。人家满山哥姓杨,跟她蒲棒儿甚的边儿也挨不上。人家是帮忙来了。人家吃没吃好,睡没睡好,一天价忙乱得手脚不着地。你蒲棒儿就知道哭,就知道哭!人家的爹还在野地里搁着哩,你不让人家回火山,你让人家到哪里去?人家埋完老人就出口外去呀。火山村的杨满山说,他再也不回这穷地方来了! 可是,她离不开满山哥。这些日子里,她听惯了满山哥的声音。满山哥大声吆喝,该办的事情就顺溜溜地办成了。满山哥说叔你忍着,她爹的病就好了,伤口就结了痂了。满山哥数落她来,那都是为了她好。别说是慢声细气,就是提起拳头瞪大眼睛训她骂她,她也一百个愿意! 没有满山哥,这日子还有甚的过头呢?没有满山哥,院子空了,蒲棒儿的心也空了。 她留不住满山哥,可是她爹应该留,他甚的话不能说呢? 蒲棒儿双眼紧盯住她爹,等着他说话。那时候满山哥腿都站在大门外面了,她爹却说:“走吧,满山,路上小心些些。” 听听那话!走吧,满山! 你当是打发长工打发讨吃要饭的呢!你就不能留满山哥多住几天? 听听那话:走吧,满山! 满山哥走了。满山哥临走没和她说一句贴心贴肺的话。 怨不得蒙古女人说:“为朋友不为你们口里猴,三春期来了九十月走。” 怨不得娘老唱:“交心不要交给走口外的人,那才是竹篮篮打水一场空!” 满山哥就那样扯开流星大步走了。蒲棒儿气得两眼生泪,扭头回到杨满山住过的烂窑里,呜呜地哭起来。 她爹送人回来,在院里喊道:“蒲棒儿,别哭了!” 蒲棒儿憋足气顶了一句:“我想我娘哩,我就要哭!” 七 心里头难活说不成, 泪蛋蛋打得胸脯脯疼 ——河曲民歌 腊月二十三送罢灶王爷爷,蒲棒儿她爹说:“女子,上坟看看你娘去。” 蒲棒儿就在院里等着。等着她爹把封包、黄表、香火和供养用的祭品装好了,父女两人一起走。不想她爹把篮子递过来,说:“爹有点事,你一个人去吧。早点去,早点回来。” 说罢了,见蒲棒儿连步子也不挪,她爹便转过身子去,仰脸望着堡里那墩烽火台,慢声慢气地说:“你娘不在了,自个儿招呼自个儿吧。到了坟地少哭几声,往后的日子长着呢。” 蒲棒儿把脸一扭,嗵嗵嗵出了大门。 一路上,蒲棒儿觉得心里头在滴血。眼前老闪动着娘那张慈爱苍白的脸。娘摇着纺车唱得那些山曲儿,也就不断地在她的耳畔响起来:还说人家不想你,半碗捞饭泪泡起。还说人家不想你,三天没吃下两颗米。想你想你真想你,泪蛋蛋好比连阴雨。想你想你真想你,手巾巾擦泪攥水水…… 娘那些山曲儿,真是白唱了。她掏心挖髓地想着自家的男人,活着时天天盼呀想呀,如今想盼得把命也丢了,可她爹只难过了一时半会儿,就把娘给忘了。一过年,她爹保准又走呀,又到口外刮野鬼去呀。这一走三年五载,怕是连闺女也不要了! 蒲棒儿越想越伤心。这才知道活成个女儿家真是太可怜了!她要是个男人,到了这般年纪,早就到口外谋生去了。即便不走,她也能撑持起家里的事情来,她爹就不会这般小瞧她了。爹不咸不淡地说,往后的日子长着呢。可不,她才活了十八年,离摇头老婆婆那种年月还远着哩。可是一个女人家,活那么大年纪又有甚的用处呢?找上一个男人,不等把铺盖捂热,人家就鬼打铙钹般嚷嚷着走口外去呀,说是不走口外这日子就没法过了!男人一走,就把苦日子给你留下了。你白天灰眉土眼地受罪去吧,受死受活没人疼你没人亲你没人搭理你。你汗水淹了脚面,你的手成了一把锉,你种上一亩鸡爪子地,你受的脊梁骨都要断了,秋后顶多也就收上三五斗粮食。男人要是不回来,第二年能把肠子饿断。这种灰地方,往后怕是连狼都养不住了。 至于夜晚,那简直就是给女人上刑哩,简直就是往干里耗女人哩。娘在的时候,一晚上总是不停地翻身,总是不停地长出气。娘惦记着口外的,牵挂着家里的,一年到头就没个睡结实的时候。实在躺不住了,就起来摇纺车纺线线,就叨叨那些永不变样的话,就哼哼那些小刀子一样的山曲儿。一句一刀,一刀一句,就把娘的心割碎了。方围几十里地界的女人们,心都让那种山曲儿割碎了。小小一个罗圈堡,哪一年都有女人疯了、傻了、痴了、死了。象这样的日子,长和短有甚的两样呢! 过完年,爹一准走呀。埋一个是埋,埋两个也是埋。倒不如早些些死了,让爹把自己埋在娘身边,他走了也就放心了。 一想到死,蒲棒儿不哭了。她跪在娘的坟跟前,眼睛不由地瞅着山脚下的黄河水。自古以来,那里就是收留苦命人的地方。闭住眼往河里一跳,就任甚的事情也不管了,就再也没有不舒心的时候了。娘总是说,蒲呀,娘把你生错了。这一辈辈生错了,那就等下一辈辈吧。蒲棒儿来到这世上,刚刚过了十几个年,娘就去了,爹又要走,她还活什么呢?她还为谁活着呢? 她挣扎着站起来,窝憋在心里的委屈一时间烟消云散。她捋捋头发,打定主意跳河去呀。 就在这时候,娘坟头上的引魂幡,刷拉拉地响作一团,满山哥突然就站在她跟前,结结实实地对她说:“人活在世上,甚的事情也得顶着!” 蒲棒儿身子一软,颤声喊道:“满山哥!” 满山哥却象烟一样飘走了。 一只老鹰在头顶上旋来旋去,只等着她倒下来,美美地吃上一顿。蒲棒儿一见这阵势,心底呼地窜上来一溜火星子:“把你个瞎了眼的挨刀鬼!你娘娘我还活着哩,你孙子倒想打牙祭!”随手从篮子里抽出一只碗来,刷地往天上一扔,老鹰拍拍翅膀,恼悻悻地飞走了。 蒲棒儿醒过神来,看天,天蓝盈盈地。看娘的坟,坟头上有她新按的手印。看堡里那墩烽火台,顶天立地不知道站了多少年了。再低头看一河流水,还是那样不紧不慢地往前流着。 蒲棒儿想:“我可真是鬼迷心窍了。多少人都活着,为甚么我偏要去死?我为我爹我娘活着,为我自己和满山哥活着。人在世上,谁就没个三灾六难?迈过这道坎坎,下一步就顺当了。山背后的日子比天长,不信往后就活不出个人样儿来!” 从坟地回来,蒲棒儿低倒头进了院,慢慢儿往窑洞挪去。在坟头哭了半天,头沉得好歹抬不起来,身子也象让人抽了筋。好不容易推开窑门,蒲棒儿嘴里念叨说:“我睡呀,长长地睡上一觉,再起来就有精神了,我就好好地活!” 进了门,一眼看见姑姑笑眯眯地坐在炕上。姑说:“蒲,姑姑看你来了!” 蒲棒儿一愣怔,软着身子扑过去,抱住姑姑又是一通哭。 蒲棒儿她爹蹲在炕沿边,咬着羊腿棒骨做的水烟锅,噗噗噗地直往出吹烟团儿。等她哭够了,她爹嗵一声跳下炕,说:“蒲棒儿,不要哭了,让你姑给你梳头吧。” 窑洞里很暖和。蒲棒儿懒懒地依偎在姑姑怀里。姑姑给她洗脸。姑姑给她用丝线绞了脸上的汗毛。姑姑还给她修了眉毛,剪了指甲。姑说:“蒲,姑姑再给你洗洗身子。” 蒲棒儿憨憨地答应了。 洗过身子,姑让她换上新衣裳。姑还给她梳了个蓬蓬松松的抓髻头。姑把她打扮的象天仙女一样。蒲棒儿很开心,咯咯咯地笑着说:“姑姑,你迷窍了,又不是娉人哩,你给我梳个这头!” 姑说:“心肝儿,你说对了。今儿是我娃的喜日子。你爹把你许出去了,许给火山村的杨满山了。两家子苦命人,也用不着瞎讲究。趁着腊月消闲,就办了吧。过一会儿,你满山哥就接你来呀!” 蒲棒儿脑子里嗡地一声,软软地出溜在炉台下面。 小毛驴得得儿走,把蒲棒儿驮进杨满山的小院里。一路上蒲棒儿想跟满山说说话,都让他给止住了。 满山哥低声说:“你爹就在后头跟着哩。你悄悄儿地,甚也不要说。” 我爹那人!娉闺女哩,当老子的也跟上了!走的时候,蒲棒儿听见姑姑劝他:“哥,你这是翻穿皮袄,连个里外也不分了。你跟着去,就不怕人家笑话。” 她爹站在院子当中,咕咕咕喝完一碗酒,然后把碗一撂,朗声说道:“妹子,你还不知道走口外的人?走来走去把家走塌了,日后连自己的骨殖都不知道撂在哪儿,还怕别人笑话?我去看女儿女婿,没人笑话咱!妹子,好好儿过你的日子,哥走啦!” 说罢,背抄着手,不紧不慢地跟在毛驴后头。 到了火山村,蒲棒儿她爹在满山院里转了一圈,然后要了半颗熟羊头一锡壶酒,跑到杨家祖坟去了。他对蒲棒儿说:“我去见见你死去的公公婆婆,我给他们道一声喜去。你们只管办你们的事,不要来泼烦我。” 蒲棒儿她爹再没回来。他托人带了个话,说是到口外找一个叫道尔吉的蒙古朋友去了。 成婚第二年,河曲县大旱,到秋后勉强能收回点籽种来。蒲棒儿对满山说:“哥,明年一开春,你就走吧。老人们说得对对地,守住妹妹倒是好,没有银钱过不了。到了口外,你先找道尔吉,就肯定能找到我爹。赶秋后你们一搭搭相跟上,平平安安地回来。” 满山点头答应了。他没告诉蒲棒儿,在口外那地方,至少有一万个蒙古人叫道尔吉。 蒲棒儿也忘了告诉杨满山,道尔吉是个唱蒙古调的,她爹一准是跟上那人卖唱去了。 (长篇小说节选,有删改) 原载《天津文学》.2月号 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年版晋军崛起精品典藏之燕治国卷《小城》 《走西口》人物剪影:蒲棒儿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:http://www.13801256026.com/pgzl/pgzl/2850.html |
当前位置: 竹篮 >走西口人物剪影蒲棒儿
时间:2022/12/31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故事丈夫女下属对我态度奇怪,仔细观察老公
- 下一篇文章: 长沙女子投资金士力佳友C胞水损失四百